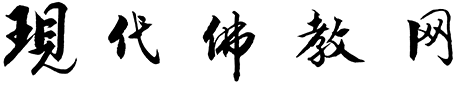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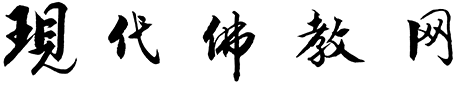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来源:佛学研究时间:2019-11-05
佛教美术比佛教思想晚出,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时出现于印度次大陆,公元1世纪时逐渐向外传播,并于7世纪以后在东南亚诸国开花结果,形成佛教美术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12世纪末期,因为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原因,佛教文化逐渐在在印度本土消亡。佛教美术虽然在印度本土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存,但因它从1世纪起一直在不断地向东南亚诸国传播,也就保证了佛教美术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在东南亚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佛教美术得到了繁荣的和富于特色的发展。
佛教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势必会遇上与其它民族传统文化相碰撞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印度佛教美术后来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渗透并发生变异的特点,佛教文化在其移植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这样的规律:早期一般保持着明显的印度风格,到中、晚期后便不同程度地民族化或土著化,有些地区和国家出现了佛教文化衰落的势头,如我国汉地、朝鲜、印度尼西亚等;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却以鲜明的民族风格使佛教美术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如我国的西藏、尼泊尔、缅甸、泰国等。
佛教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也会掺入其它文化的因素,例如印度佛教美术经中亚传入东亚时便明显带上了西域之风。而当它再向东进最后抵达朝鲜、日本时又染上了浓重的唐朝佛教美术的性格。同样,印度佛教美术通过尼泊尔或克什米尔再进入西藏时,就不免多了些雪域地区的美术痕迹或因素。
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严格地说并非只有南传和北传这两条线索,而是呈现为一种放射性的扩散状。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暂且按照南传、北传这两条传播线索来叙述。一般而论,北传是指佛教文化在尼泊尔、中亚、西域、中国、 朝鲜和日本及越南(部分地区)等国家或地区,以大乘佛教文化的传播为主;南传是指印度佛教向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传播,如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越南(部分地区)、老挝、柬埔寨及印度尼西亚等,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为主。
一、北传佛教美术的传播与发展
北传佛教美术一般认为以大乘佛教和密宗为主,但实际上印度教、小乘佛教等美术也时有发现。北传中的尼泊尔因与印度相毗邻,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诸教派都曾对它有过很深的影响,而尼泊尔佛教美术又曾经深刻地影响过我国西藏境内的藏传佛美术。北传这条线索严格说来应该从中亚(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开始,顺着兴都库什山脉逐渐东进跨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西域,经由汉地又向最东端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本文主要叙述的是除印度、中国佛教美术以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美术现象。
(1)尼泊尔佛教美术
佛教文化同尼泊尔有不解之缘。加德满都有阿育王时代建造的大佛塔和贵霜王朝样式的菩萨像,说明尼泊尔很早就有佛教文化之根基。不过印度教、耆那教同样也影响过尼泊尔。历史学家就曾发现4世纪时尼泊尔的印度教神像雕刻。尼泊尔真正兴盛佛教大概是7世纪左右的事,先是笈多样式,后来更多受波罗王朝密教美术的影响。“波罗样式”在印度消失后在尼泊尔却依旧发展,并持续了很久。
如果说早期是尼泊尔佛教美术向西藏渗透并对西藏佛教美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从唐王朝时即已开始,在12—14世纪时更为明显),那么15世纪以后佛教文化的传播则呈逆向运动,藏传佛教美术的样式,诸如金铜雕刻和唐卡绘画反过来又较多地影响了尼泊尔,并使两者的文化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尼泊尔的佛教美术主要体现在建筑和雕刻艺术门类上,绘画则不多见。其佛教美术的塔寺大都集中在加德满都。以斯瓦扬纳寺大佛塔最为驰名(大约建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巨大的覆钵体上建一四面方形塔,塔身每一面上都有一双巨眼,极具特色,令我们想起西藏江孜白居寺大塔的造型。
(2)中亚佛教美术
帕米尔山脉的兴都库什高地之北为中亚;西南为印度南亚次大陆;之西则是西亚的两河流域。这里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的文化在这里汇合之后,便带上了一种神奇的色彩。7世纪以前这里主要受三种文明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以前波斯人的阿开密尼文明的渗透以及3世纪以后波斯萨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再度抬头;公元前3世纪左右亚历山大军队带来的泛希腊化文化的影响;2世纪左右佛教文化的东传。也就是说伊朗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影响过这里。
鉴于中亚这片土地文化的多重性格,佛教文化的确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且主要局限于兴都库什山脉以南一带,旃陀罗、巴米扬为其代表性遗存。
旃陀罗指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即从塔克西拉到纳伽拉哈尔的这块地区,主要流行于2—8世纪),阿育王时期这里的人们已开始信奉佛教,但佛教美术的高扬是在与泛希腊文明相撞之后,并在2—3世纪的贵霜王朝时期进入繁荣期,以后它又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直到8世纪中亚一带被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化为止。
旃陀罗佛教雕刻与印度本土的雕刻相比,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一是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二是因为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对轮回、涅槃这类遥远而又不可企及的宗教境界远不如印度本土的人们那样地熟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首先把佛陀诉诸于形象,将他“历史化”、“人格化”。这里显然还潜藏着一种朴素直观的民众艺术特点。旃陀罗佛像厚重强壮,人物面部带有中亚人种的特征,佛相深远沉寂,头髻有明显的西方艺术影响的痕迹。
旃陀罗愈往西去,受波斯的影响也就愈重,这在巴米扬石窟美术中尤为明显。巴米扬的西大佛高达55米,面部已被破坏,但伟岸、坚实的躯体与带有装饰意味的袈裟衣纹仍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东西两大佛内龛壁上尚保存着珍贵的壁画。结实有力的线描与明暗晕染法相结合,菩萨的面容呈4分之3的比例,身体呈S型的扭曲,这些都是典型的中亚风格。
(3)朝鲜佛教美术(5—14世纪)
据史书记载,在朝鲜史的三国时代(5—7世纪),佛教美术开始正式传入。尤其百济独特的佛像雕刻最为突出,呈现为一种古拙的“百济佛微笑”样式。7世纪后半叶新罗统一朝鲜,佛教美术迎来繁茂,以石雕石塔最为众多,也许可以算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一种变体。石雕受中国北周隋风的影响,却不乏有新罗石雕特有的庄重典雅的样式。石窟的雕刻中著名的如来坐像和十一面观音像,这是此时期的代表作。新罗的石塔朴实而又独特,一般为3—5层,留下了不少纪念性遗存。新罗时代还独有一种奇特的“鬼瓦艺术”,其想象力之丰富,手法之诡密,堪称一绝。
10世纪初—14世纪末叶的高句丽时代是朝鲜佛教美术的盛期,美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佛画与佛寺上。而石雕石塔已失去新罗时代那种雄浑朴实的阳刚之气。高句丽佛画倒是十分地精致,配色颇有特点,往往是朱衣上配置精美的金泥唐草纹样,或在浓绿底子上施以金线轮廓,形成高丽的装饰风格,佛寺乃本土与唐风样式的折衷,但更加典雅秀丽。
14世纪末随着朝鲜进人李朝时代,文化整个地儒教化,佛教文化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朝鲜式的文人画。
(4)日本佛教美术(6世纪中叶—12世纪末叶)
6世纪中叶,日本朝廷正式引入佛教文化,飞鸟白凤时代(6世纪中叶—8世纪初叶)为早期佛教美术发展时期。佛寺与佛像雕刻明显受中国北魏的影响,但早期的止利派的木雕已显露出特色,以至木雕以后成为日本佛像的一大传统。佛教建筑以奈良的法隆寺为代表,其中尚保留少量早期佛教壁画,为隋唐与西方趣味的折衷,色彩颇为明丽。
天平时期(710—794年)为日本佛教美术发展期,在中国盛唐之风和朝鲜新罗美术的直接影响下,日本形成了天平美术丰满华丽的古典风格。唐招提寺、东大寺等建筑具有明确的日本古典美,其雕刻也有不少杰作。
当日本历史进入平安时期(794—1192年)后,政治文化的中心转入京都奈良一带,此时因佛教美术更具贵族宫廷色彩而被称之为“王朝美术”。“王朝美术”品味高雅而细腻。平安后期的美术(894—1192年)在日本美术史上地位极为重要,民族风格即“和风”在此时正式形成(“和”指日本民族,即“大和”民族)。佛教美术中开始显示出日本民族独特的创造才能。佛教建筑开始同唐风样式拉开距离,并逐渐形成日本建筑独特之美——幽静清丽的特色。佛教雕刻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式的“一木造”佛像(用一根木头直接塑造而成)。丰满略胖的躯体与静寂温和的面容是“和风”的特征。
9世纪初,最澄、空海两位大师从唐朝返回日本时分别建立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绘画便转为密宗绘画为盛,更以两界曼荼罗和真言祖师像为众。日本不少古代密宗寺院中尚保存着此时的密宗曼荼罗绘画,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日本的密宗美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为我们今天了解唐朝时中国密宗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间接的资料。另外日本早期佛教美术的遗存主要是建筑与雕塑,绘画作品的遗存较少,因此这类绘画作品的保留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日本佛教绘画主要保存在密宗绘画之中。
除此之外,日本佛画多与书法艺术相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美。12世纪末叶,日本进入幕府时代,佛教美术逐渐向民间美术发展。
二、南传佛教美术的传播与发展
南传以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为主,不过也有不少地区有大乘与密宗流行过,尤其是缅甸还一度特别流行过藏传佛教的密宗美术。
(1)斯里兰卡的佛教美术(前3世纪—至今)
与印度次大陆一衣带水的斯里兰卡一直信奉的是上座部佛教。公元前4世纪—9世纪1500年间,岛国之都是阿努拉陀普拉,这里留下了在规模上凌驾于埃及金字塔之上的、世界最大的若干个佛塔(均为砖瓦造),它们大多直径都在100米以上,佛塔样式与印度早期佛塔相同,为严格的覆钵形,但一般不设栏。
9世纪以后,首都移至阿市东南约80公里处的波隆纳尔瓦。波市也以佛塔建筑为主,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势都远不如阿努拉陀普拉的大塔。
斯里兰卡的佛像雕刻不甚发达,绘画仅存西基里亚(狮山岩)的摩崖壁画“云上散花女群像”(5世纪左右),但其造型的优美,手法的娴熟却可与印度阿旃陀壁画媲美,极为著名。
(2)越南与老挝的佛教美术
越南从地理上分为南越与北越,北越首都河内在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南越首府西贡在文化上则多受南亚印度的影响,可谓泾渭分明。
南越(中国古书上称“林邑”或“占波”)大约在8世纪左右时,统治阶层中开始流行印度教,信奉湿婆大神,同时并行佛教,建有印度教寺院群(8—11世纪)和大乘佛教寺院(875年),建筑风格与印尼中部爪哇时期及柬埔寨前吴哥时代的建筑有共同之处,雕刻则更多受印度美术影响。
老挝与泰国接近,故流行上座部佛教,多佛塔寺院,佛像亦为泰风。
(3)缅甸的佛教美术
缅甸、泰国同属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国度。
缅甸与印度接壤,南亚文明的影响相当明显。缅甸早期历史不明,但印度各种宗教诸如小乘、大乘佛教及至密教、印度教似乎都有过渗透。历史真正明了是从克欣族人建立的勃固王朝(1044—1278年)开始。此王朝由于特别热衷于佛教建筑的营造,故有“建寺王朝”之 美称,其建筑代表着缅甸佛教美术的黄金时期。可以说缅甸目前留下的重要艺术遗址都是勃固王朝的产物。建筑以塔堂建筑为主,塔为高塔形,数量之多达5000之众,十分壮观。勃固的它宾纽寺、阿难陀寺的诸塔都有巨大的钟形覆钵顶,建筑表面都被涂成白色,晶莹洁白,十分美丽。
勃固寺院群中的遗址,多为佛传的浮雕图,上面往往施以绿釉。寺院的墙面与天井布满了保存良好的壁画。勃固壁画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性格,既有大小乘佛教美术人物诸佛菩萨,又有印度教的忿怒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绘画显示与藏传佛教美术之间的关系,从这类壁画的风格和流行的时间来看,它主要是受西藏古格文明的影响(不过从风格上看,似与西部拉达克的美术,尤其是12世纪以后的某种地方风格之间有着更为明显的联系)。
(4)泰国的佛教美术
泰国是一个佛教美术相当兴盛的国度,主要信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与印度教也流行过。泰国文明分早晚两期,早期(5—7世纪)以小型青铜佛像为主,样式呈印度笈多风格,面孔却是泰国孟族人的特征。后期主要由泰族人完成(13世纪以后)。泰族来自中国西南,在同化了那里的先住民之后便成了统治阶级。泰族的佛教美术颇具独特风格,建筑以穹窿加尖塔为主,一种为内部实心的印度式佛塔,另一种是在高坛上设塔,其形状犹如炮弹耸立,这样的建筑大多集中在13—14世纪。佛像雕刻多为青铜像,表面打磨得很光滑,体态优美,面部有泰族人特征,有民族特色。
(5)柬埔寨的佛教美术(1—15世纪)
东南亚诸国佛教美术中最具特色的是柬埔寨佛教造型艺术。克梅尔人那种特殊的艺术天份与热烈强劲的创造欲在佛教艺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柬埔寨历史比较早的记载是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扶南国(1—6世纪)。那里出土过汉代的铜镜、印度的佛像以及罗马帝国的金币,说明扶南国曾是繁华一时的国际港口,其鼎盛期为5世纪。但好景不长,据汉文典籍记载真腊人是在7世纪时灭扶南国,并建立了著名的克梅尔王朝(6—13世纪),柬埔寨迎来了佛教美术最辉煌的吴哥时代。
前吴哥(7—8世纪)王朝的历代诸王主要信奉湿婆教,早期出土的毗湿奴神像,却全然没有佛教曾经流行过的迹象。代表着吴哥时代(11—13世纪)的鼎盛是佛教宫殿吴哥瓦特的建立(1117—1150年)。之后又建造另一佛塔建筑群——巴庸,但只有吴哥瓦特是无与伦比的。该建筑规模宏伟雄大却又极为协调美观,是克梅尔人为世界留下的伟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塔林呈炮弹形,层层叠叠,壮丽而又深邃。吴哥瓦特内有极斑澜绚丽的浮雕群,若干层回廊的壁面布满了浮雕,最长者达700米,高为25米,浮雕均为高浮雕,既有绘画的表现性,又能非常巧妙地表现出立体感,内容多为印度的两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纳》,也有柬埔寨的传说故事,每一个场面都充斥着无数的人物与动物,构图极满,不留空隙,画面生龙活虎,跃跃欲试又极为错综复杂,一种生命的活力,紧张而兴奋的情绪洋溢其中,最美丽的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是婀娜多姿、翩翩起舞的天女像。
克梅尔民族的这一伟大创举在1413年泰族的入侵下被迫遗弃在热带雨林之中,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者又重新将它发现。
(5)印度尼西亚的佛教美术(7—16世纪)
在东南亚能够同吴哥瓦特比肩的只有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一个巨大的石造立体坛城。
古代印尼史不明之处甚多,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些南印度安达罗美术样式的遗迹。7世纪到16世纪,印尼伊斯兰教化以前的这一千年是印尼佛教文化的流行时期。佛教美术主要流行于爪哇岛,其中650—930年为前期,亦称“中部爪哇时期”,是佛教美术的黄金时期;930—1530年为后期,即“东部爪哇时期”(政治中心从中部移至东部),为民族化时期,但也开始出现某种衰势。历代王朝并不都信奉大乘佛教,也有信奉印度教的,因此前期的宗教美术中有种综合的性格,不过印度教与佛教这两者似乎并不冲突,它们一般总是和睦相处。这种综合性格就表现在印尼最为出色的佛教建筑遗迹——婆罗浮屠上(760—84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立体曼荼罗,建造在3座人工建造的小山丘上,下面台基的一层平面呈方形,上部有三层圆形台阶式金字塔,每层的回廊都由大量的浮雕圆雕构成。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石造雕刻作品,给人以震撼之美,而大量的浮雕又以其精湛优美的手法创造出东南亚佛教美术世界中不朽的巨作。
10世纪以后的600年间,印尼佛教美术进一步民族化、土著化,美术风格从中部爪哇时期的纪念碑式的雄伟风格转向更加亲切温馨、更富于诗意的土著风格。但那雄浑的气魄和富于幻想的热情却逐渐衰竭。东部爪哇时期的代表作有王宫门前的守护神巨型石雕。
总而言之,亚洲的佛教美术以纷呈多样的美术式样极大地丰富了东方美术。宗教美术虽然是宗教文化的一种衍生物,却同样为人类文明,为世界的艺术史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以宗教的力量所创造的宗教艺术同样体现出人类各个民族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宗教美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会随着宗教的变化而消失,它是对我们人类文化的永久馈赠。
(作者张亚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中心讲师。)
编后:佛教美术是世界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芭,随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外传播,作为佛教文化现象之一的佛教美术也开始流向亚洲各国,对各国的文化艺术产生至深的影响。本文只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大致勾勒出除印度、中国佛教美术以外的其它各国佛教美术的基本形态、历史和特征,有助于使我们对佛教美术有一个通盘式地鸟瞰,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佛教美术的特点,还可以参看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黄夏年主编《世界宗教名胜》(佛教部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