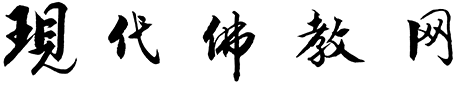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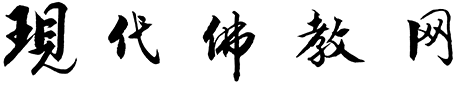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来源:微信公众号微言宗教时间:2020-08-10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早在隋唐时期便已互派使者。唐朝是当时亚洲文化中心,故此日本以模仿唐人为时尚,而这也是中华文化真正大规模地东传日本的年代。佛教作为最重要的文化之一,也在这时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佛教不单是一个宗教,更是一种新文化的象征;而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媒介,汉字以及写经艺术也传入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日本人开始习汉字,日本书法也受写经艺术的影响,跳过篆隶阶段直接从楷书阶段开始。作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写经艺术也成为“以艺术形式成就宗教文化交流”的佳话。
本文主要从写经艺术的角度,探析唐代早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情况。
一、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写经
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官方和民间均有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作品数量极为庞大,尤其是当时官方组织的写经活动规模最大,在所用纸张、装帧技艺、抄写质量等方面的规格也是最高的。
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诏令:“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而风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魏徵:《隋书》)此批写经中,纸张、抄写形制均相同;卷末均有题记,格式以及内容基本相同,通常是记录抄写人、用纸数量、校对人、典经师(官府写经机构的主管)。
早在北魏时期,官方的写经制度就相对成熟,包括严格控制纸张数量,记录写经的每个环节,而且还有明确的薪酬制度以及对于错抄、漏抄的情况的罚款制度。隋代的官方写经制度更是逐渐完善,由于写经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校经人员也开始专门化,大多为熟悉佛教经典的寺院僧人,此外还有官员加以监写。唐代则基本沿袭了隋代写经制度。
从现存史料来看,在隋唐时期,官方寺院以及僧人一直都是写经的重要主体:寺院僧人对佛经比较熟悉和了解,礼佛念经也是日常功课,加之寺院藏经丰富,所以官方写经也多由寺院僧人来完成。此外还有专门负责写经人,他们并非一定是僧人或者信徒,比如日本僧人空海记载长安求法时“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藏经”,其中就有大量的“官经生”,大多数为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术刚刚出现,尚未广泛运用,故此文书的抄写工作十分重要而且工作量很大。《唐六典》载秘书省有楷书手80人,弘文馆有25人,此外各级行政单位属下皆有“书手”“楷书手”等职务的设置。虽然不能确切知道他们具体抄写的内容以及职务,但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佛经抄写。弘文馆作为唐代的书学机构,由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在各个行政单位充当书手,他们没有官衔,相当于“胥吏”。这些隶属于中央的书手抄写的佛经往往会分送到各地寺院作为范本以供再抄写,故此要求非常严格。
此外,由于官方的写经多作为文献底本之用,往往不能满足于民间需要,故此民间的写经手也是写经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由于民间写经业的繁荣,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写经铺。
综上所述,隋唐时代佛教写经制度比较完善,参与人数众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写经的种类繁多,写经事业极为繁荣。
二、早期的日本佛教写经
关于早期的日本佛教写经,有很多史料记载。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74年召集“书生”在奈良川原寺书写《一切经》。公元686年,日本现存最早的写经《金刚场陀罗尼经》书成。不过,现在留存下来白凤时代(645-710)有明确纪年的早期佛教写经只有《金刚场陀罗尼经》和《名玄论卷第六》。从这两卷经可以窥见后世日本写经的一些法度:比如纸张的规格、书写的字数都遵从中国的形制;为了“既工而速”,都用楷书书写。之后奈良时代(710-794)的写经基本都遵循这个规则。《金刚场陀罗尼经》结字严谨,字字皆从大小欧出,从用笔上则更靠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和《泉男生墓志铭》。不过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风的书法作品也为数不少,可见当时日本人除了对佛教经典的内容感兴趣意外,也开始醉心于书法的研习。
大化改新(646)之后,日本出现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之前由氏族供养的“氏寺”逐渐变为“官寺”,直到奈良时代日本中央政府在各地建造“国分寺”,标志全国寺院归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这个进程也反映在写经活动上:与从前自发的、任意的写经活动相比,此时写经活动进入国家统一管理和运行的体系里,随之而来的则是日本佛教写经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公元701年,文武天皇创立《大宝律令》,设明经、书业、算术三科。其中“书业科”记载:当时的日本人“书以流丽为尚,不以古人笔法为宗,此与唐异”。这可以算是日本书法审美形成的开端。因此,大致可以把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作为日本写经书法的分水岭。
奈良时代是日本写经活动的高峰期:《和铜经》《神龟年间长屋王愿经》都是在这个时期书写的;各种皇室的愿经以及众多名品也相继写就。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这个时期日本写经名品的书法水平并不逊色;同时又发展出一些唐代书风没有的东西,可见日本书法审美发展的自觉意识。当时写经规模很大,出现了大量书写《一切经》的活动。据《大唐内典录》和《开元录》记载,《一切经》大致为五千余卷,卷帙浩繁;而据现有文献的确切记载,当时抄写的《一切经》有24部之多,也就是这批经卷总数超过十万卷,如果再加上不可统计的寺院写经以及民间写经,可见规模空前。而一些特别流行的经典会重复抄写,被寺院用于日常诵读和供奉。
奈良时代的写经都用楷书抄写,这既便于阅读,又可以减少错漏。奈良时代有不少字体优美,并且通篇没有误字脱字的写经;而这样的写经在平安时代(794-1192)就少有出现,而到镰仓时代(1192-1333),错漏便大量见诸于经卷。这是因为早期写经并非一项贵族活动,而是佛教传播的手段,从宗教意义上来说,传抄时除了注重字体的优美,更强调内容正确,有错误的写本根本不会流传。(参见:石田茂作《佛教传播和写经》)
三、从写经艺术窥见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从写经艺术来看,当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总体特征是单向度、全方位(包括制度、艺术等各个方面)。比如,同时代日本的写经书法,从用笔到结体到章法等,都完全继承了唐人样式;当时佛教经书主要从中土东渡,而没有从日本回流的记录。
具体到写经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法层面。从书手而言,汉字书写是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的基本技能,这些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时,抄经的规矩、技法等都属于“必修课”,他们一一学习,基本以全盘接受为主,因此笔法、结体和章法都以唐样为准,然后回到日本广为传播。从书写工具而言,书写大幅风格一致的作品,除了技法之外,书写工具也必须相同或相近;而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遗存的“天平笔”正与唐代的“鸡距笔”的制法相同,与中国《笔经》所载相同,显然是仿制中国的。
2.制度层面。写经书手身份的官方认定准则、职官制度等都是沿袭中国,此外还有设置写经所、规定纸张尺寸、书写流程、审阅规程等,也是如此。例如,与唐人写经一样,为方便统计字数目和纸张数目,每行都是17字的规格;而奈良川原寺书写《一切经》,载公元691年赐“书博士百济末子善信”,这种官衔制度也源自于唐朝“书学博士”一职。
3.艺术层面。入唐求法的僧人对日本书法影响巨大,比如日本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师巨匠、被誉为“日本的王羲之”的空海,不但在中国得到佛法传承,同时也得到了书法传承,回国后成为嵯峨天皇的书法老师。此外,当时日本写经的书体使用、艺术审美等也都是全方位学习中国,比如,现在日本东大寺所藏的写经《贤愚经》与唐人写经的风格基本相同。尽管日本书法的指导思想从《大宝律令》的颁发开始就已经产生变化,但在艺术表现上还未能看到与中国写经有明显的差异,仅仅是在风格上趋向圆润(与唐代的“方折用笔”相对)。唐人的楷体写经在日本影响达百年之久,尽管日本的写经风格有一些变化,但是与同时代的中国写经书法风格几乎同步。而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此时日本的佛教写经才逐渐发展出自身的特点。
作者潘灏贤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