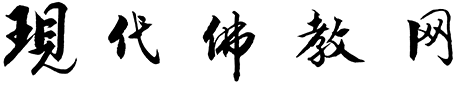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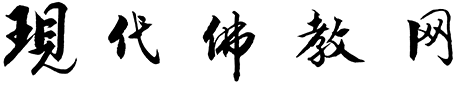
WWW.AMITUOFOCN.COM

来源:公维章著时间:2020-04-20
飞来峰造像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上,有五代至元代时期的佛教造像380余身,是浙江省最大的一处佛教造像群。位于龙泓洞洞口西侧的高僧取经组雕(第46、47、48龛),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与讨论,集中体现在对这组雕像的内容与雕刻年代的探讨,以赖天兵、劳伯敏、于硕的研究成果为代表。

飞来峰第46龛取经三人浮雕
一、飞来峰第47龛的造像组合
关于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的内容,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有“唐僧取经”和“白马驮经”两组,二是认为有“白马驮经”“朱士行取经”和“唐玄奘取经”三组。学者对第48龛反映的东汉明帝时期的摄摩腾与竺法兰“白马驮经”的内容没有疑义,对第46龛的唐玄奘浮雕也没有疑义,那么,第47龛反映的内容到底是“朱士行取经”还是唐玄奘的取经随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整体对第46、47、48龛的内容加以分析。
对佛教造像内容的确定,造像题记是分析造像所属内容的首要依据,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则考虑依据佛经及其注疏文献与画史文献来展开分析。此高僧取经浮雕现存有8条题记,皆位于竖长方形框内,其中5条题记标明附近所刻人物身份,成为分析浮雕人物身份的重要依据。现存的这8条题记是原来所刻还是后来改刻,这是解决浮雕人物身份的关键所在。
第46、47龛3条标明人物身份的题记位于人物行进方向的头部前方(人物的左前方),而第48龛中间人物的行进方向与第47龛相左,故题记所刻的位置(人物的右前方)亦与46龛不一致。根据前揭赖天兵文中的插图《第46-48龛取经浮雕平面图》所标注的题记位置,对8条题记的现状作以下交代:A题记为“□岭”、B漫漶不识一字、C为“摄摩腾”、D为“竺法兰三藏”、E为“天竺来”、F为“从人”、G为“朱八戒”、H为“唐三藏玄奘法师”。A、B、C、E题记改刻的可能性不大,争论较大的是G题记。劳伯敏认为G题记“朱八戒”中的“八戒”二字为“士行”的改刻,“八戒”二字“明显经后世重凿,但第一字‘朱’看来可能是原刻,而这正与朱士行的姓氏相符。”既然其它题记改刻的可能性不大,但改刻G题记的可能性也不会大。因为某种机缘,需要对此处题记中漫漶不识的字加以补刻,为什么A、B、C、E题记中漫漶的字不补,单要去补刻G题记的“八戒”二字?据赖天兵观察,“龛中题记,“朱八戒”三字的刀法系一气呵成,没有两个年代合成的迹象,而且题记上下表面进深均匀一致,并没有应该出现的下部的磨蚀。因此,“八戒”两字系原字磨损后改刻之说,缺乏考古学的依据,难以成立。”笔者同意赖先生的观察与分析,另外,改刻原来的题记并非易事。

飞来峰第46龛玄奘浮雕像
在敦煌壁画的榜题中有补写的情况,时过境迁,原来的壁画榜题漫漶不清了,在重描壁画的同时,也一并将榜题补写,或者只补写榜题,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石刻题记的补刻并非如壁画榜题那样容易。众所周知,古代要将文字刻于石碑或岩石上,首先由书者将文字用朱砂作墨书写于石面上,称为“书丹”。勒石工序,需要有经验的石匠来完成,古代勒石的石匠绝大多数并不识字。据笔者考察,中国古代石刻文字补刻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碑刻文字有较多空余的空白处再镌刻其它内容的文字,或者是在造像碑中有较多空余的空白处镌刻与此造像无关的其它内容的文字;二是原来石刻文字漫漶不清了,由于某些重要原因需要用原碑的拓片或抄录文字或底稿将原碑文字重新镌刻,但这种情况的补刻,都是另选碑石进行重新镌刻,并不存在在原碑石上补刻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碑或窟龛摩崖造像中,至今还没有发现将原来漫漶不清的造像题记在原题记位置进行补刻的情况。因此,飞来峰第47龛“朱八戒”题记中仅将“八戒”二字改刻成“士行”的可能性不大。
对题记“朱八戒”所属人物,劳伯敏认为是第47龛前行的第一人,“从雕凿位置看,位于题记的第一块,显然是指第一人。这个人物站在高13厘米的平台上,似作回头状,象是一位指挥者,在整组浮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惜上半身残损严重,原可能也是有头光的。”赖天兵则认为题记“朱八戒”所属人物应为第47龛中间的挂念珠、持杖棍的牵马者,“纵观飞来峰取经浮雕,人物形象都留有题记以表明其身份,题记处于龛中部一组人马的范围内,题记处于龛后部一组人马的范围内,题记的具体位置都在人物的前上方,这种规整划一的做法,没有给模棱两可的想法留下余地,“朱八戒”无疑指龛中部,而不是前部的那位人物,“从人”则是指后一位牵马者。”笔者同意以上赖天兵的分析,因为整个46、47龛的人物行进方向一致,H题记的内容与有头光、身穿袈裟、双手合十的高僧像相吻合,因此,G题记“朱八戒”即指第47龛中间挂念珠,持杖棍的牵马者;F题记“从人”指后一位牵马者。由于第47龛前行的第一人上半身残损严重,从下半身情形分析,其回头作指挥状的可能性不大,另从其残存的服饰来看,绝不同于整个取经浮雕中的三位高僧服饰,故其身份为高僧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上半身完好,其也不可能有高僧标示的头光。其前方肯定有表明其身份的题记,惜已毁失不存。

飞来峰第48龛东汉驮经浮雕
从第48龛残存图像及题记分析,反映的内容为东汉明帝时,郎中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以B题记后的人物为代表,此人面向摄摩腾作礼拜状,题记位置亦与两位高僧的题记位置不同,标明此人应面向摄摩腾)前往天竺,迎请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从天竺出发,白马驮经,行进至逼近葱岭的场面。此事件标志着佛法传入中国之始,这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碑刻中随处可见,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第46龛玄奘独身一人表示“唐三藏取经”,似与第48龛不相协调,因为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取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因此,从第47龛牵马前行的三身人物的装束来看,应该是第46龛玄奘的随从,三人的身份是行者,还不是受具足戒的僧人,绝不是学者所认为的是表现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于阗取经的内容,并且“朱士行取经这一题材在佛教艺术中似找不到先例,甚至尚找不到同例。”因此,第46龛与第47龛的关系正如常青所言,
第47龛的三身雕像均不为中国传统的僧人装束,且都身佩兵器,明显具有随行护卫的身份,行进的方向也与第46龛的玄奘相呼应。所以,笔者以为,第46与47龛应为一组,可统一命名为“唐僧取经图”。
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第48龛东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携经、像从天竺东来,二是第46、47龛联合表现的唐玄奘及其随从从天竺取经东归。此二组图像组合在一起的原因,除以上笔者所论二者皆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外,或许与南宋后期或元初杭州地区盛行水陆法会有关。
水陆法会是佛教追荐亡魂的一种宗教仪式,举行法会时,要祭奉众多的神祇,这些神祇通常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包括壁画、卷轴画、版画等。赵宋之时,水陆法会始分为南、北。在宋元明清时期,南水陆法会主要盛行于四明(今宁波)和杭州地区,其修斋仪轨即为《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每年的盂兰盆节,各地大都举行盛大的水陆法会,每会必有水陆画,起码宋元时期的杭州地区,水陆法会必有包括摄摩腾、竺法兰、玄奘在内的祖师画像,或与其他祖师共为一帧,或三法师单独一帧,因此,宋元时期杭州地区的画工是极为熟知这一题材的,将三法师各配以取经随从,将这一题材雕刻于佛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佛像集中的飞来峰,以向世人昭示取经之不易。
之所以将第47龛的三身人物称为玄奘的随从,原因是既然该高僧取经组雕的雕凿年代为元代,从现存明代以前不同阶段玄奘取经图的人物组合来看,还未见有“朱八戒”这一人物的出场。于硕通检了与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有关的文献材料,主要包括《西游记平话》、《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销释真空宝卷》与《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等,图像材料则主要为两块磁州窑瓷枕上的取经图后认为:
明代西游记壁画
记载有朱八戒的取经故事资料较为有限,或为残本,或几经修改增补,依现存几种重要的文献与图像资料推测,西游记在元明清三朝应存有多套体系,它们之间也并不孤立,而是有着一个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朱八戒人物形象可能属于诸体系中的某一支,产生于元代末期,并由《西游记》杂剧的搬演而传播开来,但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中人物形象是否为朱八戒却不能因此简单断定。依以上分析笔者怀疑,《西游记》杂剧于钱唐地区流传开来之后,可能有人将榜题改刻,但改刻的时间也不必限定在元代,因为在明初这个人物还被叫做“朱八戒”。
于硕经过详细考证,推测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的雕刻年代为元代早期,而通过对现存记载有朱八戒的取经资料的审慎考察,认为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于元代末期,据此而怀疑飞来峰第47龛的“朱八戒”题记为后人改刻。但据笔者研究,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于南宋后期或元代早期,见于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瑜伽教科仪文献《佛门受生宝卷》及相关文献。